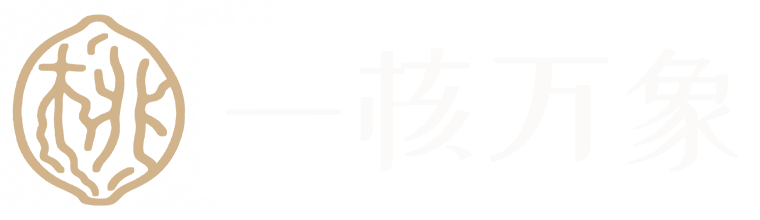老刘把桃核放在掌心,像托着一枚刚被月光晒干的月亮。壳上那层浅褐的“皮肤”还带着果香,轻轻一嗅,舌尖竟泛起去年夏天的甜味。谁想得到,这么一枚被啃完就扔的果核,竟能长出层峦叠嶂、烟波浩渺,比任何一张卷轴都更会“藏景”。
做桃核雕,最过瘾的是“拆盲盒”。外壳完好,谁也不知里面藏着什么纹。砂纸一磨,云纹、水纹、雀眼纹……像老电影突然显影,一条山脊、半汪湖湾自己浮出来。有时磨急了,把“山脚”磨平,整座山就塌成一粒沙,前功尽弃;可也有时,刀尖刚挑破皮,一股暗褐色的“瀑布”顺着纹理冲下,活脱脱一幅《观瀑图》——那感觉,跟小时候第一次把橡皮糖拉成丝一样上头。
有人问我:在0.8毫米厚的弧面上刻山水,是不是得屏住呼吸?我说,错,得先学会“喘气”。呼吸对了,手腕才不会较劲。每一刀下去,都像给核桃挠痒,它一舒服,就把藏在肚子里的风景全交出来。最妙的是“借色”,桃核尖上那点焦红,当落日;腰线一圈灰白,当烟雨;底部暗褐,当夜山。颜色自带,省得调配,老天爷早就上好色,只等人把镜头框出来。
最常被问:“老刘,你这山水能保存多久?”我掏出十年前磨的第一枚“小赤壁”,壳面早已润得像被少年把玩了整个青春期的核桃,颜色沉了,刀口却更亮。它陪我搬过四次家,掉过马桶(捞起来继续用),依旧完好。桃核不怕岁月,只怕你把它供起来——人手上的油脂、汗气、脾气,才是它最爱的“养山泉水”。
夜里收工,我把刚刻完的“桃核江山”扔进搪瓷杯,倒上半杯凉茶水,让山水自己“泡澡”。明早醒来,茶叶末会卡在峡谷里,像一叶扁舟;水面漂着极细的木屑,像远山的雾。那一刻,我总想起小时候在课本边角画小人,下课铃一响,把整页风景折进书包,沉甸甸的——如今,我把整座山水折进一枚果核,放进口袋,走路都带着轻微的哗啦声,像袖珍的浪。
想入坑的朋友,别急着买“专业刀”。先啃三斤桃,把核攒齐,拿指甲锉试试手。第一座山肯定塌方,第二座山像土豆,第三座山就会有点“山样”。等你把自家厨房的油烟机当“云海”,把案板上的刀痕当“栈道”,恭喜你,入门了。记住,桃核上的山水,不是让你远观的,是给你走路时偷偷摸一把——指腹摸到峰峦,比眼睛看见得更真。
毕竟,画纸挂在墙上,桃核揣在心上。